准确认定新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
 222
222
点击播报本文,约

近年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类犯罪产生新变化,主要表现为:犯罪手段从传统的线下非法收集获取公民个人信息,通过线上方式售卖获利,转向在部分软件中非法获取具有一定要素但不能明确界定种类性质的部分信息(如隐去特定位数的不完整身份证号码、打车记录、网购记录、不完整的手机特定时段基站定位信息等)后,通过线上非法提供的数据库内容,利用多个大数据模型等碰撞比对,根据特定买家要求予以加工分析,最终形成定制化公民个人信息,进而在线上售卖获利。
新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表现形式。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刑法该条文规定的“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通讯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新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部分行为人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大量起初不能完全符合上述标准的公民个人信息,该类信息仅具备部分真实内容,单独使用或与其他信息简单结合,不能达到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目的,但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大数据模型等工具,对这类“碎片化”信息进行碰撞比对、模型学习等加工处理,并结合部分合法获得的信息共同使用,最终可以二次生成具备特定信息要素、能够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对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构成新的威胁与挑战。相较于传统的直接获取收集行为,该行为获取信息种类更加丰富、画像更加精准。
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类犯罪案件审查起诉过程中,应高度重视上述犯罪新特点,加大针对性打击力度,特别是在犯罪情节判断中强化对公民个人信息属性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及其关联行为性质的认定。笔者认为,应当着重从以下方面判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是否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
注重审查是否具有可能形成完整公民个人信息的要素,组合比对后形成符合法律规定的信息达到“情节严重”标准。案件审查起诉过程中,首先,应系统审查在卷证据,引导侦查机关全面收集可能涉案的公民个人信息,同时严格按照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要求,规范在线提取电子数据,固定电子数据类关键证据。其次,查清涉案上下家用于比对、碰撞、生成特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方式,引导侦查机关调取程序工具使用记录和历史记录、特定数据库操作关键信息、AI学习记录、大数据模型使用购买记录等重要证据,特别是对犯罪嫌疑人供述提到的关键信息,如学习关键词、程序代码、脚本、抓包工具等,第一时间提取并固定证据。对收集到的具备一定要素但不能明确界定种类性质的信息,按照案中反映的信息生成手法,必要时可借助鉴定或侦查实验的方式,在原有条件下生成公民信息(如行踪轨迹、可识别的账户密码等)后,按照入罪证据标准(即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进行判断,确定是否具备形成完整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能,以产生特定信息的数量,作为判断是否达到“情节严重”的重要依据。
注重审查涉案信息中是否有特定信息用于犯罪目的,从而确定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为。针对涉案证据中出现的不同性质的海量公民个人信息,在审查起诉中除了需要界定信息类型之外,还要通过证据审查重点关注涉案信息可能的用途。应注重审查犯罪嫌疑人在此类犯罪中的主观目的,具体可区分为纯牟利、提供帮助参与上下游犯罪等类型。通过在卷证据反映的,存在纯牟利主观故意的,对上下游犯罪确无主观明知的,应当按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入罪标准予以判定处理。存在提供帮助参与上下游犯罪主观故意的,对于积极参与上下游犯罪并实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应当查明上下游具体犯罪类型如诈骗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确定罪名,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事实作为重要犯罪情节考虑从重处理;对于参与实施上下游犯罪但情节较轻或上下游犯罪行为无起诉必要,仅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为该上下游犯罪提供帮助的,可以根据既遂事实,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
注重审查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为中关联持有大量不能明确界定种类信息的行为以及非法获利标准的认定。在此类案件的审查起诉中,往往存在大量与获取和贩卖伴生的持有行为,该行为因违法性认识存在争议,导致入罪标准认识不清。对于该类信息贩卖后产生的获利,除直接转账交易外,实践中还存在通过虚拟币等交易的情形,以上情况的出现给查清犯罪事实带来困难。对于非法持有以上类型信息行为的违法性审查,应当根据行为所处环境,结合上下游是否存在关联犯罪行为、内容的取得是否超出正常合理获取的方式、数量和内容是否符合常理认识等,综合判断持有行为的性质,对于明显具备违法性、无合理辩解,情节严重的,应按照“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处理。对交易行为和获利的认定审查,应引导侦查机关对据以定罪的关键种类信息的交易记录进行对应,排除其他交易辩解,发现其中的洗钱线索。对于涉及的生成后用于贩卖的信息,应当按照实际获取金额确定违法所得,用于犯罪的软件购买、模型开发、大数据学习等费用可以认定为犯罪成本,但不应与实际获取金额抵扣后以实际盈利金额认定违法所得。
(来源:检察日报,作者分别为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一级检察官助理)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 评论
- 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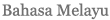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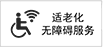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
 关注人民网,传播正能量
关注人民网,传播正能量